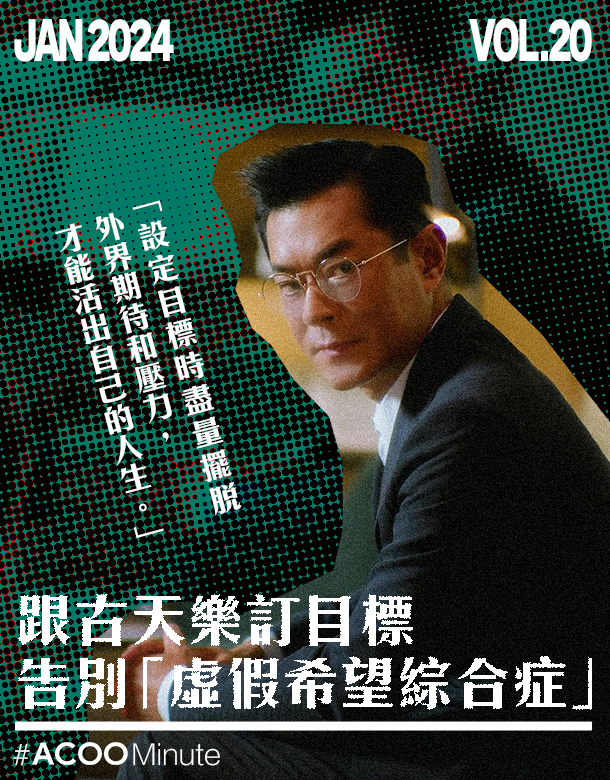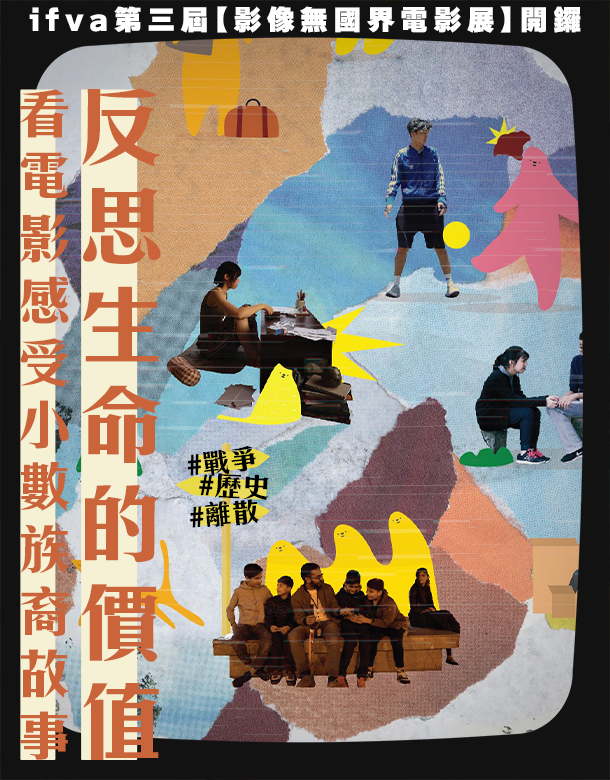【紅眼】:《蝙蝠俠》:他失眠,他孤獨,而且魯莽衝動
戲院解封,好幾部被迫延期的大片隨即填滿了接下來的檔期。單是華納旗下出品,便有《怪獸與鄧不利多的秘密》與《蝙蝠俠》兩部系列大作幾乎打對台。延期事少,兩片同樣從開拍至今都多災多難,一部易角換人,如今還被其外傳《尊尼特普與前妻的離婚官司》搶去風頭,另一部則無以為繼,舊班底四散,乾脆推倒重來,將整個系列重拍一遍。
但值得欣賞的是,最終由 Matt Reeves 執導、Robert Pattinson 主演的 2022 年新版《蝙蝠俠》,算是新人事新作風,擺脫了前一代泥足深陷的 DC 明星大亂鬥格局。至少它明顯不再是一部標榜熱血沸騰、亮麗悅目的超級英雄電影,而是一個回歸傳統的懸疑偵探佈局,更似 David Fincher 的《七宗罪》和《殺謎藏》。格局相對小一點,予人的想像空間則更大,因為這一次的主角並不是蝙蝠俠,而是 Gotham 這個罪惡之城。
在一片樸素和陰沉的灰調之中,電影不像過去十多年的前代《蝙蝠俠》那麼構圖精緻、場景豐富,卻襯托出一個骯髒多雨、腐敗蕭條,而且各懷鬼胎的犯罪都市,而且偶然被刺眼的異色光芒渲染整幅畫面,更見空洞荒涼。與此一脈相承的是,今次亦再沒有造型誇張、玩味十足的盔甲和戰車(相對減少了以商品化為目標的感覺),除了蝙蝠俠與貓女造型比較寫實,最意外的是著名反派謎語人看起來一點都不像謎語人。他完全捨棄 90 年代 Jim Curry 那個嘩眾取寵的紅頭綠衣漫畫造型,取而代之只是一名不起眼的路人甲、模仿犯,但其實就是這樣才恐怖。外表平平無奇的謎語人,甚至連反派頭目的氣焰都沒有,卻呼應了新版《蝙蝠俠》的主題,英雄與反派從來不是對立,而是因果,是一體兩面。過去為觀眾所熟悉的蝙蝠俠,總有著一顆嫉惡如仇的俠義之心,被視為正義榜樣,但其實以暴易暴、有仇必報的執念,同樣都會感染旁人,將惡意擴散。無獨有偶,跟 DC 最近另一部電視劇《正義使者》(Peacemaker)的反英雄主義不謀而合。
《蝙蝠俠》歷代版本眾多,撇除 60 年代的最早期電影改編,往後不同年代都堪稱經典。基於童年情懷,個人較為喜歡特攝味道濃厚的 Michael Keaton 版,後來「黑暗騎士三部曲」的 Christian Bale 版以至近年 DC 宇宙的 Ben Affleck 版,則感覺一般,只覺得他花招愈多,卻愈來愈扁平,單純是個有錢就是任性,擁有無限高科技玩具的中二病中年。當然,因為「黑暗騎士三部曲」的蝙蝠俠只是為了襯托 Joker 的機智和瘋狂而生的蠢貨,而 DC 宇宙的蝙蝠俠亦不過是個英雄聯盟召集人。今集也不例外,是為突顯 Gotham 的醜陋失序而生。
而跟前幾代相比,Robert Pattinson 的新版蝙蝠俠最為年輕,卻沒有過去幾代的老練傲慢,他不再是個強勢的超凡人物,畢竟這個版本的 Bruce Wayne 只是剛剛「出道」成為蝙蝠俠,急於尋人復仇,反而處處衝動犯錯,害怕身份被揭穿,而且尚未適應白天扮演花花公子,入夜之後替天行道。這個總是失眠,一臉憔悴蒼白的復仇貴公子,顯得幼稚而充滿病態。但病態美不美,符不符合觀眾心目中的蝙蝠俠形象,則見仁見智。坦白說,無疑角色設計是大膽破格的,只是演員並不投入,演出缺乏魅力,這些問題都完全寫在 Robert Pattinson 蒼白無力的臉上。當然,若是一個始終不想扮演蝙蝠俠,想跟這個正義使者形象保持距離的 Bruce Wayne,其實也不失為一種解讀。
推倒重來的《蝙蝠俠》未必能超越之前的經典系列,而且難免有觀眾嫌長達三小時的電影缺乏搶眼鋪排,沒有高潮迭起的計算。但至少它不再跟風,不是見慣見熟那些英雄聯盟大亂鬥,為早已拍爛的蝙蝠俠電影帶來一點新的轉變。
相關文章
【虛假希望綜合症】訂立目標應如古天樂:每天一小步 十年磨一劍
新年伊始,每年這個時候,總會雄心壯志地給自己定下好些目標:早點睡、做運動、多看書⋯⋯2024年剛過去7天,誠實回答:你開始為新年目標努力了嗎?即使開始了努力,這鼓熱情可能捱不了幾星期,很快就打回原形。結果每年的新年目標,都跟前一年差不多。如果你也是這樣,可能已陷入「虛假希望綜合症」(False Hope Syndrome)衍生的迴圈。 幻想很豐滿,現實很骨感。所謂「虛假希望」,就是對自我改變有不切實際的期望。在設定目標時,很易會高估自己的能力,亦可能會誤將長遠目標當成短期目標。最後因為目標太難達到,很易放棄執行;或者其實自己已有進步,但因時間不足而無法達成當初的目標,最後感到氣餒沮喪。 要打破循環,堅持直至完成目標,毫不容易。建議大家可以向古天樂學習。因為一個科幻片夢,他訂下一個「三十年計劃」,在第一個10年製作出首部港產科幻片《明日戰記》。他曾說拍攝科幻片困難重重:「需要很多錢、很多時間,但這是我的夢想,一定要堅持下去。」用10年去做一件事,看來有點不可思議。但這似乎是他的習慣——他下一個目標,是以純香港製作班底,製作《明日戰記》系列的前傳動畫電影,圓夢的同時,也希望能培養香港電影人的下一代。 這種堅持,從他的一個小習慣可見一斑。大家可能都有過寫日記或網誌的習慣,你記得自己維持了多久嗎?古天樂維持了17年。他由2006年起,風雨不改,每日寫一篇網誌,寫的是天南地北,可能是天氣,或簡單的節日祝福。儘管字數不多,但17年來能做到每日一篇,可說是毅力驚人。 從古天樂身上我們可看到:維持習慣的其中一個關鍵,是要降低努力的門檻。每天只需努力一點點,但重點是要持續每天做,就可以將習慣維持下去。不用苛求自己短時間內達成目標,因為有些目標,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才能完成。正如古天樂在今年1月4日的網誌說道:「盡可能擺脫外界的期待和壓力,堅持自己的價值觀和信念」。要記住,我們都是為自己而活。 文字:林三 @lam.three 設計:Owen @wai.ho.98 圖片來源:古天樂IG @kootinlok_louis 、劇照 -------------------- In ACOO, you can get refreshed in #ACOOMinute.
【少數族裔的人和事】 ifva《影像無國界電影節2023》 離散各有因 還得生存下去
烽火四起,在烏俄戰爭、以巴衝突的戰事鋪天蓋地映入眼簾時,世界各地的小角落也有不同大小的零星戰亂。生存在那些土地的人們,努力的掙扎求存,還望能守護家園、家人朋友的生命和信念。可是,炸彈總在夜空中墜落,子彈無情的飛來,你能想像這些畫面嗎? ifva第三屆「影像無國界電影節 2023」穿越種族、語言和性別藩籬,連結各地因歷史、戰爭或移居而經歷離散的故事,呈現人類身處差異下的生存狀態。來看看今年的放映節目吧! |《倖存少女奇蹟之旅》 開幕電影《倖存少女奇蹟之旅》以真人訪問、默片片段及動畫製作,把一次世界大戰期間,一位少女在亞美尼亞大屠殺中的倖存經歷,殘酷慘痛的過去重現於銀幕,提醒人們毋忘歷史。 |「流轉家園」短片節目 離開家國的人們,在異鄉又是如何自處? 在精選五部紀錄片及動畫製作的電影會找到答案。紀錄片有以烏克蘭孩童視角映照德國歷史的《寧靜潛行》、美墨邊境尋親之旅《嫲嫲》、華人家庭紛爭《團團圓》;而動畫電影有聚焦在法國移民的《安心之所》,及由眾人回憶編織出葡萄牙裔垃圾收集員艱苦人生的《夜冷佬》。 |「絲打同盟」短片節目 精選五部由本地及海外女性導演的作品,以不同故事來描繪一群少數族裔女性如何在創傷中成長,走出自己的人生路,短片包括講述湯加與澳洲混血女孩尋找身分認同的《Hafekasi》、刻劃美華裔移民家庭的《姊姊》、在挪威港人的同性戀故事《祝君安好》、巴勒斯坦裔舞者面對以巴衝突的《臨行前跳舞》,和兩位黎巴嫩藝術家講解法國性別與勞動的殖民史的《絲蜜絮語》。 |長片節目《國界蒸發》 導演以異鄉人的角度拍攝,講述一座地中海小島塞浦路斯的移民故事,感受一個外來者如何尋找歸屬與認同。 |閉幕電影《幸運餅乾製作中》 導演為伊朗裔導演 Babak Jalali,故事以美國歷史最悠久的阿富汗社區為背景,講述原為美軍基地翻譯員的阿富汗少女的移美生活。 今年電影節繼續關注本地少數族裔,除了放映由少數族裔青年創作的短片,更首辦展覽及真人圖書館,與觀眾分享他們在地的生活經驗,一同探索及反思自身的獨特價值。 |同場加映:本地少數族裔青年作品 《Boju》講述居港尼泊爾嫲嫲Boju獨自照顧年幼孫子的故事,一次意外後改變了嫲孫二人的的生活,展示世代之間無法分割的聯繫;而另一部影像作品為《Blurry to me》,故事是一個在新環境中迷失的女孩,嘗試尋找自己的真正歸屬和身份。 「影像無國界電影節2023」 日期:即日至12月10日 詳情:ifva@hkac.org.hk
【港版返校】天黑請閉眼 驚嚇後的心寒餘韻 港式鬼片《七月返歸》導演謝家祺:「想做不只是讓你嚇一跳的香港恐怖片。」
不知道大家對港式鬼片有甚麼印象,可能是暗藏一些小道理的《陰陽路》系列、由人氣偶像主演的《古宅心慌慌》或《校墓處》,抑或可稱為藝術新高度的《殭屍》等。不過,仔細想想,有哪一部恐怖電影能打破那堵大銀幕的界限,讓寒意蔓延並滋長到心中、發顫砭骨? 「身為這一刻的恐怖創作人,我就是跟着時代的走向。」導演謝家祺說。2017年,他在本地電影製作及發行公司mm2舉辦的「第一屆新晉導演計劃」脫穎而出,時隔5年多,終推出其首部編導電影《七月返歸》。同為恐怖片迷的他,希望故事去掉驚嚇還能載道,所以劇本一直卡關、砍掉重練,總之就是感覺不對,謝家祺靜默後道:「在我身處的香港,感受的恐怖……最初和今天,有一種不同的改變。」 對於重度恐怖片迷而言,或許《七月返歸》的驚嚇仍不足夠重口味。不過,在公屋屋邨、都市傳說、童年回憶小遊戲等,謝家祺試圖打造一座奇異的驚慄世界。如同江𤒹生(Anson Kong)飾演的「向榮」,在承認並擁抱那雙看似不幸、卻能讓你更接近真理的陰陽眼時,便會看到被重重包裹在「鬼」背後的真正老大哥。 文字:Hoiyan (@seamouse_hoiyan) 攝影:Mak (@iunyi_) 設計:Owen (@wai.ho.98) |跟着時代走的恐怖電影導演 mm2第一屆新晉導演計劃的得獎者,分別為李駿碩(Jun)、林森和謝家祺。按電影公司原定安排,謝家祺應是第一位完成拍攝並上映電影的導演,豈料卻成最後一位。《七月返歸》的劇本,足足「磨」了4年才有了雛形,他的沮喪一一看在老闆及監製文佩卿眼內,前者說:「不如在書中抽幾個喜歡的故事拍,我也很有信心。」而文佩卿也曾說:「阿Jun在後期,阿森只差一個ending就寫完,你變成失蹤人口了。」謝家祺直言,那時候真的很卡。 「這幾年對恐懼有一個新體驗,所以便不斷fine tune、不斷尋找,所以用了很長時間。」謝家祺認為,身在香港所感受到的恐懼改變了,他心中的劇本高度需要回應時代,這注定是一場艱苦的筆戰。回想起多次的砍掉重練,謝家祺坦言故事並非受特定事物剌激出現,而是一個沉澱結果,他說:「社會運動時,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感覺,我沒有特意去回應那個當下,覺得是過份感性、太衝昏頭腦的。」那些感覺並未隨着時間前進而被淡去,而是一直在消化、轉換形態,「它原來一直burn住,然後那些東西就連結起來,連劇本也連結起來。」 就這樣,在2021年初落筆完成《七月返歸》後,謝家祺默默地捎去電郵通知監製文佩卿,他笑言:「我不敢WhatsApp直接找他,你永遠不知道那(劇本)可能是一堆垃圾。」誰知道,它真成了垃圾,只因大半個月後毫無回音,謝家祺一問後,文佩卿滿頭問號:「稿?有稿嗎?你交了稿?」才知道,電郵掉進垃圾郵件。 |片場貨真價實的鬼故事 故事背景設定於愛民邨,由於拍攝期間在疫情時期,所以欲租借廢置屋邨的計劃只能擱置,謝家祺說:「美術很厲害,搭了這個大部分人都覺得很真的屋邨景。」然而,這是一部鬼片。如果是你的故事,你也會希望了解一下,人之尚情,鬼自然也不例外,畢竟祂們也曾是人。 「這件事沒有太多人知,砌景時頻頻出意外,有人跌傷了手,又有人在工廠大廈樓下被絆倒。」謝家祺分享拍攝過程貨真價實的鬼故事,常言道:「鬼可怕,但沒貨交更可怕。」監製文佩卿只能找來師傅指點迷津:「是呀,上面有4隻。」謝家祺猶記得在拍攝第一或二天時發生的事,「拍攝時看着mon,感覺到有人拍了我膊頭兩下,cut機回頭看並問『誰叫我?』,結果附近都沒有人。」完結後,文佩卿才說,那天有一位「好朋友」跟着他,不過師傅已把祂「殲滅」。謝家祺表示,聽罷一陣愕然:「我不是害怕,而是想為何要殲滅祂?如果祂是我爺爺怎麼辦?」 |成為導演前,先學會演員的語言 不過,對於謝家祺而言,印象最深刻的不止片場鬧鬼事件,還有和監製文佩卿一起上演技課。身為負責天馬行空的編劇,且是執行製作的導演,謝家祺在《七月返歸》的崗位偶爾感覺像自己打自己。為了讓編的創作不受影響、執行能讓演員清晰訊息,文佩卿決定和他在林立三博士的演技課,一起學習演員的語言,這一切從了解何謂演戲開始建立一套「身同感受」,謝家祺說:「所有事要關乎角色出發,關乎解決問題,即不是有多開心,而是為何那麼開心。」而導演與演員之間,也不是指令式的溝通,反而更應該提供更多空間給後者發揮,而這就能從電影結局一幕看到。 「開始時,我避開不和他(AK)討論結局那場戲,先進入整個故事。」謝家祺表示自己和AK也是電影新鮮人,所以雙方的交流和相處也毫無輩份或身份的芥蒂。由於整個拍攝是順拍,所以整個劇組上下也是一起經歷了男主角向榮(AK飾)的心路歷程,所以在最後一場戲時,謝家祺對AK說:「這個moment就是你的,沒有direction給你,你做吧!」那時候,旁邊有工作人員曾問謝家祺「情緒是否要更濃?要不要更興奮?」,他的回應是:「不用了,給AK多一次機會便可。」這一次,AK把所有情緒都釋放出來,謝家祺說:「他有,也知道其選擇,已經有自己一套理解。」 平心而論,AK首次擔正的演出雖仍顯生澀,但傾盡全力的演出,交出完整的自己予電影,戲迷也應能從劇情推進之中深刻感受到,謝家祺說:「尤其他那麼忙,又要演唱會又要跳舞,很感謝他百忙仍抽空一起看很多reference、思考角色,真的很into這件事。」 |不只嚇一跳的What the Fuck Moment 回到劇情,《七月返歸》有不少香港人熟悉的元素,像是屋邨、粵劇花旦、都市傳說如「九廣鐵路」和「打生樁」,還有不少人的兒時遊戲「狐狸先生幾多點」等,都是謝家祺的心思。 「這些很iconic、經典的鬼故事,我很怕有一天會沒有人知道、相信這些意想不到的力量是存在、好奇或覺得神秘,其實是少少的保育。」他解釋「宇仔之死」為民間傳說「打生樁」:「或稱為『塞豆窿』,愛民邨也有,就是犧牲小朋友來換取這地方的安穩,是很自私的。」謝家祺曾思考父母的思路,他們是真心為了更好的生活而奉獻孩子嗎?若不想,又需要承受怎樣的目光呢?然而,電影中的宇仔並不是第一個成為供品的孩子,也不會是最後一個。 整個劇情中,沒有一個成年人死去,謝家祺說:「他們只是進行了『返歸』的儀式。」割舌自盡後,經歷彌留,便能留入美麗新世界。那麼,「為未來着想」的保險銷售員(林善飾)也沒有死嗎?謝家祺回答:「他也沒有死,但他其實也像鬼一樣,每天重覆坐地鐵、sell保險,那個人就是你我他。」活着和死去,你分得清嗎? 如果你能撕掉鬼怪製造的魅惑,便可以獲得導演埋藏的彩蛋。有些觀眾說,看畢電影不知為何會眼濕濕;謝家祺笑言,這是自己很喜歡的觀影體驗,原以為只是被嚇,卻找到很多訊息:「我稱之為『What the fuck moment』,所以也很想在香港恐怖片做不只是嚇你一跳的東西。」 |面對恐懼的M底屬性 電影結束在第二天,第一天就是回到現實反問觀眾:「你的第一天是怎樣呢?」 對了,不說不知道,其實謝家祺真的非常M底,他雖說非常喜歡恐怖片迷,但其實怕的不得了:「我非常害怕,那些suspense moment(下一秒可能就是驚嚇場口)我會看着角落,但我又會很享受那個緊張。」雖然他並未有回答,但相信他的第一天,便是坐在電腦前繼續敲打着鍵盤、老氣的在筆記本上書寫突如其來的靈感。面對不一樣的恐懼,即使非常害怕,也會找到專注的位置,想盡辦法樂在其中吧!
【七月返歸】鬼片包裝的苦口良藥 導演謝家祺、AK江𤒹生建美麗新世界 「不說出來、扮看不到,那就是一個正常人。」
「只要見Mirror有份出現,你就知道,這個節目必定會變為業餘、不認真,和像馬戲團。」只要內容是關於男子組合Mirror的討論區帖文,便很大機會看到這句留言。雖然他們擁有強大號召力,卻也有製作團隊因其「偶像」形象而退避三分,就像江𤒹生(AK)差點因為此原因,便與《七月返歸》失之交臂。 2017年,本是網絡作家出身的謝家祺aka中環塔倫天奴aka離奇家遮,從本地電影製作及發行公司mm2的第一屆新晉導演計劃脫穎而出,得到一份電影合約。謝家祺終經歷6年的劇本輾轉反側,終在今年農曆七月推出其執導的首部大銀幕作品《七月返歸》。縱使恐怖電影對某些人而言代表沒有深度,這他卻不這麼認為:「恐怖故事比ETV更有教育意義,雖然會用驚嚇或鬼神包裝去嚇你,但往往包含了很重要的普世價值。」 在各種的未被看好下,二人得到一個機會。謝家祺和AK也交託出自己的100%,導演笑言:「(有場戲)他激烈得甚至撼穿頭。」每一個真實的讓人心寒的鏡頭,劇本的每一個段落,也是他們用盡全力證明這不只是一場90分鐘的鬼話連篇。離開戲院時,每個人也會得到一雙澄淨的陰陽眼。 文:Hoiyan (@seamouse_hoiyan) 攝:Mak (@iunyi_) 起點.劇本與角色 影後座談會,監製文佩卿曾提及,初期選角是特地避開Mirror成員的。「對,因為劇本是恐怖片,若找一個偶像明星,不知道普羅大眾會否覺得是青春偶像恐怖片,青春笑下驚下那種。」導演謝家祺聽後解釋。開始試鏡後,主角「向榮」一角鎖定於30歲左右的男演員,曾找來不少素人和演員,讓導演不禁想:「我也是監製給機會,才能拍電影。即使他們是男團,是否也應該給一個公平的機會呢?」 之後,AK透過公司得知mm2將進行電影角色試鏡,在細閱取得的半份劇本後,先對「向榮」(電影男主角角色)一見鍾情,他笑說:「以往的角色可以找到一些自己的性格特質,但向榮是沒有的,這很有挑戰性。」然而,最讓AK感興趣的是劇本的主題,他細細的分享讀本後的感受:「很多人面對一些問題會視而不見,這部電影用陰陽眼去討論,到底應否繼續裝作看不見呢?這是我很喜歡的中心思想。」衝着對劇本和角色的莫名喜愛,他在第一次試鏡前已去求教戲劇指導老師袁綺雯(Yem)。 換到導演謝家祺的視覺,第一次試鏡時有20多個與AK的同齡演員,他說:「在試鏡時的溝通,很connect到我們。」最後謝家祺和監製選擇了AK,或許是他在了解角色時,成功捕捉到向榮的一縷靈魂,而這部分也從未被發現,導演說:「他對向榮的解讀、想法和疑問,也令我再work on多一點在角色的特質中。」 AK與向榮的重疊 謝家祺說,最深刻的是AK分享個人靈異經歷時淡然:「其實幾恐怖,但他說的像是別人經歷的事一樣。」而向榮也正正是這樣的性格,與世界拉開距離,並瑟縮在最陰暗的角落觀察。 那是發生在多年前,AK還住在梨木樹邨舊居時的事,那天他與朋友準備一起去踢足球:「舊式屋邨是電梯在中間,我住在左邊走廊的單位,走去電梯口要經過其中一個單位。」正在那時候,朋友直指該單位外有一位身穿白衣服的姐姐,AK回頭看到祂後,一個瞬間便消失不見,他便心想:「這麼古怪?」但小朋友一心只想去玩,便甩頭就忘了這件事,直到回家後才跟母親訴說。「是不是你看錯了?」對於媽媽提出假設,AK補充因踢球時怕碰撞弄壞眼鏡導致受傷,所以通常頂着近視眼去玩,但他非常肯定自己是真的看到祂。 之後,AK便生病了,「我嫲嫲還在生的時候,是在深水埗賣元寶蠟燭的,她弄了一些符水給我喝,之後就好像沒事了。」AK的爸爸打聽,原來那個單位在一個多星期前發生了跳樓命案。直至搬離那個家前,AK也沒有再遇見那個祂。 謝家祺筆下與AK視覺中的向榮 《七月返歸》是謝家祺的心血,筆下的向榮更如他的兒子一般,他坦言:「這種熟悉,有時可能成為我的盲點,而AK也在解讀向榮裏提供了很多見解。」謝家祺舉例,劇本初稿的向榮是更抽離於世界:「小時候他會跟朋友、媽媽分享見鬼經歷,但久而久之別人會覺得因為『看到』,你會否才是問題所在?」而他的媽媽(白靈飾)不顧家徒四壁,也不斷嘗試找尋方法把兒子變回「正常」,也讓向榮感到內疚:「慢慢他會發現世界原來是這樣運作的,不說出來、扮看不到,那就是一個正常人。」但AK則認為:「總有一些東西能打動到他,例如宇仔。」因為這個角色很能代表小時候的向榮,所以在二人之間的相處,向榮會不自覺地流露溫柔一面。 為了更好的準備角色,AK花了不少心思在研究角色的童年世界,以建構整個角色的性格,完整其人物小傳:「如果我是他,我會很怕媽媽。」AK回想,出現在向榮生命中的人不多:「同學、一些道士、媽媽,還有一個從未出現過的爸爸。」直至角色長大後也沒甚麼朋友,而這麼多的關係中,AK認為向榮與媽媽的關係最為深刻:「二人相依為命,也因為向榮的一些年少無知、衝口而出的話,破壞了母親的幸福,或是其本身家庭的原有樣貌。」從小犯的錯、創傷都落在角色的心中,既一直未有解決,也找不到宣洩的渠道,便成為了長大的向榮。 共同架構角色世界:撻指甲 「與演員的溝通中,我不想要一種導演指令式的方法,告訴演員應該怎樣做、或者應不應該害怕,而是希望一起進入角色的狀態,找出這刻遇到的問題、為甚麼要害怕。」謝家祺說,因為他與AK同是電影新鮮人,二人於公於私也會不斷溝通,AK接言:「我們用了很多時間去討論向榮的童年,即使知道有一些故事,仍然要在當中找到不同細節去放大。」而「撻手指甲」便是其中一個共同成果。 電影有一幕是白靈為年幼的向榮剪指甲,卻不小心剪到肉讓其受傷流血,AK認為這可能是角色童年的小創傷,感覺可以將此放大。劇組之間的討論後,便把動作變成角色的小動作,謝家祺解釋:「剪指甲是一個充滿母愛的動作,其實是很象徵的,有些人用錯方法去愛,便會不小心傷害了你,成為一個陰影。」即使傷口癒合,向榮總會在焦慮、緊張或無聊時不自覺的觸碰,他續言:「這是我們一邊談着向榮、一邊理解時,因應作出改動的東西。」 給予100%的自己:傳說中七樓的那場戲 走出角色的內心,回歸劇情本身,恐怖鬼片當然要令人感到毛骨慄然才痛快!而這也是第二次試鏡的重頭戲,謝家祺認為男生演出「驚戲」更有難度:「因為做得不好,會被人感到很懦弱或沒有說服力,所以我很貪心,直接讓AK試了七樓那場很激烈的驚戲。」或許未是最完美,但導演在過程中看到他的情緒起伏和可塑性。 確認出演機會後的AK也未有鬆懈,持續找戲劇指導老師Yem學習,他分享一個方法:「簡單來說,如果呼吸急促時,人可能會比較緊張;如果呼吸很平淡,我說很怕也沒有人信,所以有些小方法快速進入狀態,但後續還是要靠幻想和導演的guideline幫忙。」即使拍攝現場的置景氣氛恐怖,但拍攝團隊人多勢眾,對演員而言是很難進入狀態,所以AK會把自己關在道具升降機中:「關上門全黑,想以前看過的電影情節、不同鬼的樣子、蛇蟲鼠蟻,可能5至10分鐘再出去拍。」 對於AK而言,經驗不足亦影響了其信心,拍攝時亦無暇跳出角色審視表現,他說:「只能盡力呈現當下感受到的,其他便交給老師、導演和監製。」以AK躺在碌架床上格被鬼壓一幕為例,導演會先說明這場戲及呈現的畫面,正式拍攝時則會給他聲音導航,AK說:「一直會有一把聲音說話,白靈姐姐在後面、位置去到哪裏、現在慢慢逼近你,我聽着這些guideline再加入幻想,還有Yem老師的呼吸法。」 但最讓謝家祺深刻的則是傳說中「七樓那場戲」,笑說:「攝影師對他說『仔,close-up先做嘛』,你自己說一下這個撼穿頭的故事。」AK接着說,那場戲前已拍了很多害怕的狀態,而這一場戲是向榮其中一個最怕的時刻,他便想:「怎樣可以令到這個驚更突出一點呢?」想着便直接行動,把頭直接撞到門上,停機之後大家都說:「Okay、Okay!你有沒有事?」其實只是有一點痛,導演插嘴:「流了一點點血。」AK笑說攝影師椰子走來對他說:「傻豬,剛剛是wide shot,但效果是okay的,等一下close-up再來一次好嗎?」 終章:第一天 19天的拍攝結束,完成後期製作後,誰想想不到電影的首映在紐約——第22屆紐約亞洲電影節競賽單元,AK坦白道:「之前mm2已send給我看了一次,因為想在訪問時能回答。」他亦說,不論私下或電影節觀看成品時,自己總是在看不同的位置:「可能和其他演員的對手戲或自己的狀態不好,所以不是最好的表現,會放大這些瑕疵。」中文科補習名師林溢欣曾說,搏盡無悔之重在於「盡」,AK的演技是否最好留待業內人士及觀眾評定,但他至少已在內外的表演中用盡全力。 而對於導演謝家祺而言,這部電影是完夢之作,也是他創作的新起點,他說:「一直都想成為恐怖片導演,所以才不斷寫小說、拍恐怖短片,其實都是練習。」終在大銀幕看到作品,整件事夢幻得很。 步出戲院,思考自己的決定 訪問的最後一個問題:「如果以個人身分進入故事,最後你會願意交換某些條件,生活在這個美麗新世界嗎?」AK一頓再說,每個人也有權利選擇自己的善良,但每個人心中善良的尺也不一樣,不能以己度人:「你問我的話……我應該不會選擇那個新世界,我還是會堅持自己,做一些覺得正確的事。」謝家祺則表示,他的答案如向榮:「電影最後的第一天是留給我們,回到日常,而日常又是怎樣?」AK說:「無論經歷的事情是甚麼也好,90分鐘最後的抉擇是留給各位觀眾自己體驗。」 而你,又會否願意付出代價,交換一張生活於美麗新世界的門票? Lorraine Lam @HairCulture Yumi Cheung @Annie G. Chan Makeup Centre 服裝:Y-3, Giuseppe Zanotti 造型:PIPA Creative 場地提供: 太子酒店
【香港角落】跟着5部港產片懷舊遊
8、90年代,港產片風靡全球,以殭屍、古惑仔、當時生活文化為題材,拍成警匪片、周星馳喜劇或港式浪漫愛情等,角色、價值觀、對白、歌曲至今仍繼續影響着亞洲各國的影視。 時間來到2023年,香港的風景雖未必如同昔日,但依舊動人。如果你忘了這些畫面,不如跟着我們,找一個周末時光重遊舊地。 攝:Mak (IG @iunyi_)
【電影命】 如何煉成《正義迴廊》、《死屍死時四十四》 導演何爵天的運氣與實力:「很難複製別人,最後仍是做好自己。」(上)
電影,不論是對於演員、幕後工作人員,抑或製作人,這個屬於大銀幕的舞台絕對是一座夢工場,每一格影像,也是以眾人燃燒生命的意志拼砌而成。 何爵天,半年內上映導演生涯的首兩部電影——《正義迴廊》和《死屍死時四十四》,前者更以4300多萬票房成為香港三級片最高票房電影,更為他奪得今年金像獎「最佳新導演」,惟躲在獎項背後的,雖然已成昔日故事,但說起來仍言猶在耳。 「這麼多年,我的平均月薪不可能過2萬,戶頭存款也從未多於10萬。」何爵天的青春,就是在片場、或在看電影中度過,賺來的錢也花在拍攝上,捱了10年卻不曾有放棄念頭,他亦甘之如飴。說着說着,他突然大笑起來:「不,我得獎有獎金,現在有10萬了。」現實很磨人,但只要走進電影世界,內心的小孩又能跑出放肆,歡迎來到何爵天的夢工場。 文:Hoiyan (@seamouse_hoiyan) 攝:Mak (@iunyi_) 踏進校門前先走進戲院 「我猜是2、3歲已經入戲院看電影。」被問到何時開始接觸電影,何爵天拋出一個讓人腦袋當機的答案,他續言:「是《小魚仙》或《鐵鉤船長》,你數回年份吧!」輕輕在手機螢幕上點按數下,搜索引擎便跳出前者的上映年份為1989年,那年他的確是2歲。 一個尚未正式入學讀ABC的小男孩,已經被家人拐進戲院,何爵天解釋:「告訴我看《忍者龜》,誰知道進場是呂良偉的《跛豪》。」雖然他只是個孩子,但已能分辨「想看」和「不想看」的電影:「很多成人向的電影,也有一兩套迪士尼,我記得《鐵鉤船長》是自己想看的。」 泥足深陷電影路 升讀中學後,何爵天認識了一些同樣喜歡電影的同學,每個星期更一起組隊看早場。在戲院以外,他也開始在LD碟(鐳射影碟,80至90年代中期的電影儲存媒體)、VCD中探索電影世界:「正版、老翻也好,甚麼都好,總之經常看電影。」 何爵天就讀的可風中學為地區名校,但他在初中時已清楚自己志不在書本,反而喜歡創作:「曾打算去學畫漫畫,但畫得很差,最後也沒學成。」喜歡籃球,卻自覺身高和球技不如人,又只能放棄;最後,何爵天鎖定了從小喜歡的電影,找到了屬於自己的目標:「電影相對能遲起步一點,但我相對比同齡人早起步,而且看戲量也一定比別人多。」因為喜歡電影、渴望創作,加上看到很多導演也是「紅褲仔」出身,更讓他肯定這條路:「香港都係紅褲仔,史匹堡也沒有畢業。」之後,他進入忘我狀態看電影,沉醉得不能自拔,但他也很快看到現實,當代電影工業怎樣也要讀電影,他說:「讀電影是一個強烈的慾望。」 畢業後,何爵天考入浸會大學副學士,目標原校升讀電影系,始終書本還是成為了絆腳石,他說:「又要讀中六、七的東西,GPA不夠分又玩完,所以去報讀演藝。」兜兜轉轉,但洗濕了頭,還要是自己的夢想,難不成現在才要放棄嗎?對於何爵天而言,能通往夢想的話,這絕對是一條單程路:「浸會兩年,演藝四年,所以前前後後也讀了六年電影。」 真.電影人生 從畢業到首部電影《正義迴廊》登上大銀幕,中間隔了一整個10年。何爵天回憶初出茅廬第一部參與的電影:「我做場記,好像有$6000一個月。」他說得雲淡風輕:「其他行業應該很快有2、3萬,但我這麼多年的月薪平均也不會超過2萬。」難道,夢想真的能變成麵包?還是電影人真的能光合作用? 「其實你不太需要花錢,因為跟劇組是沒有生活的,反而這樣才能儲錢。」何爵天笑笑解釋,雖然聽着有點怪,但又似乎很有道理。不過,正常人在工作以外,應該也有自己的生活、娛樂?「我最大的娛樂就是看電影。」語畢,他思考一下再說:「自費旅行,在這10年也不知道有沒有3次。」即使戶頭儲了些錢,但拍攝的每個鏡頭也是錢,所以基本上何爵天的所賺和支出也是內循環:「所以我戶口永遠也不超過10萬元。」突然想起,才拿到金像獎最佳新導演,他大笑道:「剛剛贏獎金有10萬了。」 真要說上電影以外的興趣,何爵天表示也喜歡看書、聽音樂,但好像最終還是圍繞着電影。「沖咖啡!我有特地報班去學沖咖啡。」他突然靈機一觸,這應該能與電影切割了吧?「我也想開咖啡店,但我希望咖啡店能加入電影元素,可能夜晚做放映場地。」 10年揼石仔之路 十年的路不好走,誰也不知道機會在哪一個轉角靜候,也有人搏上一生也遇不上它。「中間有一個時間真的很辛苦,被罵得很厲害、壓力很大,停了一年沒跟電影。」身為一個「電影痴」,何爵天腦袋裏從來沒有冒出過放棄,他只是看到「首部劇情計劃」和「年輕導演」的成功例子,嘗試為自己開闢一條新路:「很想拍自己的東西,很想快點跳過一個門去做導演。」這一年裏,他在不斷努力中自省,感悟當初高估了自己的才華:「同時努力也很重要,一步登天沒甚麼可能,或許有人可以,但你怎麼知道他背後花了多少努力?」既然無法複製別人的公式,那便繼續「揼石仔」做好自己。 又經過幾個寒暑,何爵天接到由翁子光監製的香港電台外判劇集《獅子山下》,負責其中一集《高價收購》,劇長45分鐘,近乎半部電影的時長。合作過程中,翁子光對何爵天甚為賞識,邀請他為其工作,並開始釀釀開拍何爵天的第一部電影,這是何其幸運的事!「一定有運氣,但又不可以將所有東西歸咎運氣,不是我有能力,他也不會給我機會。」的確,片場云云之中都是有電影夢的人,但即便有能力,又是如何讓別人看到自己?何爵天分享:「我跟了他兩部電影,也付出了很多時間,直頭起居生活也幫翁子光處理。」在2016至2020年期間,就這樣一點一滴累積,用行動和作品來替自己說話:「這個世界沒有吃不吃虧,應該是付出多少時間,就得到多少東西。」 何爵天認為能成就這段緣份,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,他說:「他看很多電影,如果聊電影,自己看不多的話,根本聊不來。」 屬於我的夢工場 《正義迴廊》劇本的原型事件發生於2015年,翌年何爵天曾開始初步建構故事和研究主角,因為《風再起時》擱下劇本兩年,在2018年才又重新開始。 舊港產片年代,其實不乏精彩的奇案片,像《八仙飯店人肉叉燒包》,何爵天說:「那些都是比較官能的。」某程度上,他認為翁子光開擴了奇案片的類型,站在受害人角度、以文藝愛情手法拍攝的《踏血尋梅》,甚至《正義迴廊》也是翁子光提出的意見:「不是只賣弄血腥,用法庭這個載體去解構這個奇案。」因為劇情圍繞在法庭,為了感受審訊氣氛和了解法律程序,何爵天到法庭報到了兩個月,他說:「有些案件從第一天聽到最後判決。」歷時差不多三年時間,何爵天作為導演的第一部電影終於開鏡。 「我寧願挑戰或踏前一步,寧願失敗,也不想重覆做。」這是何爵天對電影題材和拍攝的堅持,可見《正義迴廊》突破性地打破場景,為演員演出、時間空間也帶來變化;又挑戰死亡與屍體的禁忌,接下黑色喜劇《死屍死時四十四》,走進別人的劇本,再賦予它自己的靈魂。 下一篇何爵天導演的訪問,一起走進他的兩部電影,解構他製作時的心路歷程。 【電影命】 每步求突破 劇本、剪拍燈光、置景、演員 開箱製作電影中的何爵天:「重覆去做沒有意思。」(中) 【電影命】 導演的命題—平衡自己、觀眾與票房市場 何爵天的創作本源:「憤怒。」(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