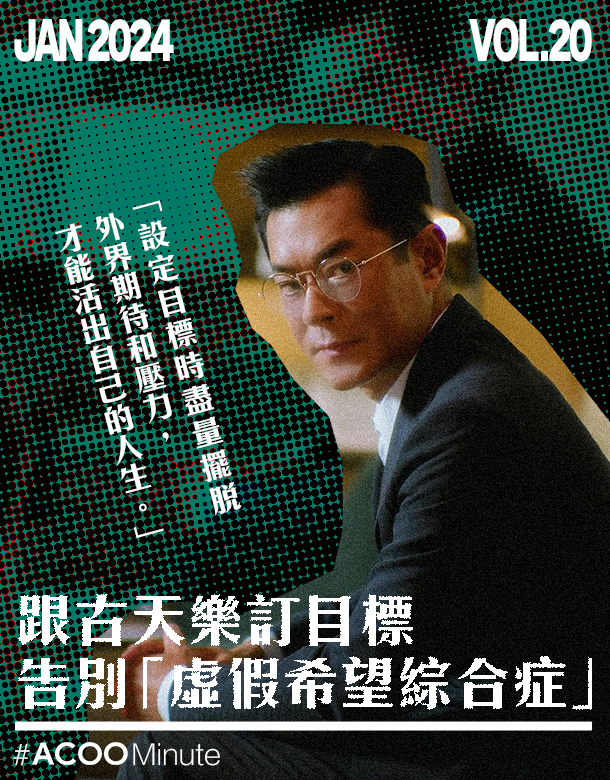【七月返歸】鬼片包裝的苦口良藥 導演謝家祺、AK江𤒹生建美麗新世界 「不說出來、扮看不到,那就是一個正常人。」
「只要見Mirror有份出現,你就知道,這個節目必定會變為業餘、不認真,和像馬戲團。」只要內容是關於男子組合Mirror的討論區帖文,便很大機會看到這句留言。雖然他們擁有強大號召力,卻也有製作團隊因其「偶像」形象而退避三分,就像江𤒹生(AK)差點因為此原因,便與《七月返歸》失之交臂。
2017年,本是網絡作家出身的謝家祺aka中環塔倫天奴aka離奇家遮,從本地電影製作及發行公司mm2的第一屆新晉導演計劃脫穎而出,得到一份電影合約。謝家祺終經歷6年的劇本輾轉反側,終在今年農曆七月推出其執導的首部大銀幕作品《七月返歸》。縱使恐怖電影對某些人而言代表沒有深度,這他卻不這麼認為:「恐怖故事比ETV更有教育意義,雖然會用驚嚇或鬼神包裝去嚇你,但往往包含了很重要的普世價值。」

在各種的未被看好下,二人得到一個機會。謝家祺和AK也交託出自己的100%,導演笑言:「(有場戲)他激烈得甚至撼穿頭。」每一個真實的讓人心寒的鏡頭,劇本的每一個段落,也是他們用盡全力證明這不只是一場90分鐘的鬼話連篇。離開戲院時,每個人也會得到一雙澄淨的陰陽眼。
文:Hoiyan (@seamouse_hoiyan)
攝:Mak (@iunyi_)
起點.劇本與角色
影後座談會,監製文佩卿曾提及,初期選角是特地避開Mirror成員的。「對,因為劇本是恐怖片,若找一個偶像明星,不知道普羅大眾會否覺得是青春偶像恐怖片,青春笑下驚下那種。」導演謝家祺聽後解釋。開始試鏡後,主角「向榮」一角鎖定於30歲左右的男演員,曾找來不少素人和演員,讓導演不禁想:「我也是監製給機會,才能拍電影。即使他們是男團,是否也應該給一個公平的機會呢?」
之後,AK透過公司得知mm2將進行電影角色試鏡,在細閱取得的半份劇本後,先對「向榮」(電影男主角角色)一見鍾情,他笑說:「以往的角色可以找到一些自己的性格特質,但向榮是沒有的,這很有挑戰性。」然而,最讓AK感興趣的是劇本的主題,他細細的分享讀本後的感受:「很多人面對一些問題會視而不見,這部電影用陰陽眼去討論,到底應否繼續裝作看不見呢?這是我很喜歡的中心思想。」衝着對劇本和角色的莫名喜愛,他在第一次試鏡前已去求教戲劇指導老師袁綺雯(Yem)。
換到導演謝家祺的視覺,第一次試鏡時有20多個與AK的同齡演員,他說:「在試鏡時的溝通,很connect到我們。」最後謝家祺和監製選擇了AK,或許是他在了解角色時,成功捕捉到向榮的一縷靈魂,而這部分也從未被發現,導演說:「他對向榮的解讀、想法和疑問,也令我再work on多一點在角色的特質中。」

AK與向榮的重疊
謝家祺說,最深刻的是AK分享個人靈異經歷時淡然:「其實幾恐怖,但他說的像是別人經歷的事一樣。」而向榮也正正是這樣的性格,與世界拉開距離,並瑟縮在最陰暗的角落觀察。
那是發生在多年前,AK還住在梨木樹邨舊居時的事,那天他與朋友準備一起去踢足球:「舊式屋邨是電梯在中間,我住在左邊走廊的單位,走去電梯口要經過其中一個單位。」正在那時候,朋友直指該單位外有一位身穿白衣服的姐姐,AK回頭看到祂後,一個瞬間便消失不見,他便心想:「這麼古怪?」但小朋友一心只想去玩,便甩頭就忘了這件事,直到回家後才跟母親訴說。「是不是你看錯了?」對於媽媽提出假設,AK補充因踢球時怕碰撞弄壞眼鏡導致受傷,所以通常頂着近視眼去玩,但他非常肯定自己是真的看到祂。
之後,AK便生病了,「我嫲嫲還在生的時候,是在深水埗賣元寶蠟燭的,她弄了一些符水給我喝,之後就好像沒事了。」AK的爸爸打聽,原來那個單位在一個多星期前發生了跳樓命案。直至搬離那個家前,AK也沒有再遇見那個祂。

謝家祺筆下與AK視覺中的向榮
《七月返歸》是謝家祺的心血,筆下的向榮更如他的兒子一般,他坦言:「這種熟悉,有時可能成為我的盲點,而AK也在解讀向榮裏提供了很多見解。」謝家祺舉例,劇本初稿的向榮是更抽離於世界:「小時候他會跟朋友、媽媽分享見鬼經歷,但久而久之別人會覺得因為『看到』,你會否才是問題所在?」而他的媽媽(白靈飾)不顧家徒四壁,也不斷嘗試找尋方法把兒子變回「正常」,也讓向榮感到內疚:「慢慢他會發現世界原來是這樣運作的,不說出來、扮看不到,那就是一個正常人。」但AK則認為:「總有一些東西能打動到他,例如宇仔。」因為這個角色很能代表小時候的向榮,所以在二人之間的相處,向榮會不自覺地流露溫柔一面。
為了更好的準備角色,AK花了不少心思在研究角色的童年世界,以建構整個角色的性格,完整其人物小傳:「如果我是他,我會很怕媽媽。」AK回想,出現在向榮生命中的人不多:「同學、一些道士、媽媽,還有一個從未出現過的爸爸。」直至角色長大後也沒甚麼朋友,而這麼多的關係中,AK認為向榮與媽媽的關係最為深刻:「二人相依為命,也因為向榮的一些年少無知、衝口而出的話,破壞了母親的幸福,或是其本身家庭的原有樣貌。」從小犯的錯、創傷都落在角色的心中,既一直未有解決,也找不到宣洩的渠道,便成為了長大的向榮。

共同架構角色世界:撻指甲
「與演員的溝通中,我不想要一種導演指令式的方法,告訴演員應該怎樣做、或者應不應該害怕,而是希望一起進入角色的狀態,找出這刻遇到的問題、為甚麼要害怕。」謝家祺說,因為他與AK同是電影新鮮人,二人於公於私也會不斷溝通,AK接言:「我們用了很多時間去討論向榮的童年,即使知道有一些故事,仍然要在當中找到不同細節去放大。」而「撻手指甲」便是其中一個共同成果。
電影有一幕是白靈為年幼的向榮剪指甲,卻不小心剪到肉讓其受傷流血,AK認為這可能是角色童年的小創傷,感覺可以將此放大。劇組之間的討論後,便把動作變成角色的小動作,謝家祺解釋:「剪指甲是一個充滿母愛的動作,其實是很象徵的,有些人用錯方法去愛,便會不小心傷害了你,成為一個陰影。」即使傷口癒合,向榮總會在焦慮、緊張或無聊時不自覺的觸碰,他續言:「這是我們一邊談着向榮、一邊理解時,因應作出改動的東西。」

給予100%的自己:傳說中七樓的那場戲
走出角色的內心,回歸劇情本身,恐怖鬼片當然要令人感到毛骨慄然才痛快!而這也是第二次試鏡的重頭戲,謝家祺認為男生演出「驚戲」更有難度:「因為做得不好,會被人感到很懦弱或沒有說服力,所以我很貪心,直接讓AK試了七樓那場很激烈的驚戲。」或許未是最完美,但導演在過程中看到他的情緒起伏和可塑性。
確認出演機會後的AK也未有鬆懈,持續找戲劇指導老師Yem學習,他分享一個方法:「簡單來說,如果呼吸急促時,人可能會比較緊張;如果呼吸很平淡,我說很怕也沒有人信,所以有些小方法快速進入狀態,但後續還是要靠幻想和導演的guideline幫忙。」即使拍攝現場的置景氣氛恐怖,但拍攝團隊人多勢眾,對演員而言是很難進入狀態,所以AK會把自己關在道具升降機中:「關上門全黑,想以前看過的電影情節、不同鬼的樣子、蛇蟲鼠蟻,可能5至10分鐘再出去拍。」

對於AK而言,經驗不足亦影響了其信心,拍攝時亦無暇跳出角色審視表現,他說:「只能盡力呈現當下感受到的,其他便交給老師、導演和監製。」以AK躺在碌架床上格被鬼壓一幕為例,導演會先說明這場戲及呈現的畫面,正式拍攝時則會給他聲音導航,AK說:「一直會有一把聲音說話,白靈姐姐在後面、位置去到哪裏、現在慢慢逼近你,我聽着這些guideline再加入幻想,還有Yem老師的呼吸法。」
但最讓謝家祺深刻的則是傳說中「七樓那場戲」,笑說:「攝影師對他說『仔,close-up先做嘛』,你自己說一下這個撼穿頭的故事。」AK接着說,那場戲前已拍了很多害怕的狀態,而這一場戲是向榮其中一個最怕的時刻,他便想:「怎樣可以令到這個驚更突出一點呢?」想着便直接行動,把頭直接撞到門上,停機之後大家都說:「Okay、Okay!你有沒有事?」其實只是有一點痛,導演插嘴:「流了一點點血。」AK笑說攝影師椰子走來對他說:「傻豬,剛剛是wide shot,但效果是okay的,等一下close-up再來一次好嗎?」

終章:第一天
19天的拍攝結束,完成後期製作後,誰想想不到電影的首映在紐約——第22屆紐約亞洲電影節競賽單元,AK坦白道:「之前mm2已send給我看了一次,因為想在訪問時能回答。」他亦說,不論私下或電影節觀看成品時,自己總是在看不同的位置:「可能和其他演員的對手戲或自己的狀態不好,所以不是最好的表現,會放大這些瑕疵。」中文科補習名師林溢欣曾說,搏盡無悔之重在於「盡」,AK的演技是否最好留待業內人士及觀眾評定,但他至少已在內外的表演中用盡全力。
而對於導演謝家祺而言,這部電影是完夢之作,也是他創作的新起點,他說:「一直都想成為恐怖片導演,所以才不斷寫小說、拍恐怖短片,其實都是練習。」終在大銀幕看到作品,整件事夢幻得很。

步出戲院,思考自己的決定
訪問的最後一個問題:「如果以個人身分進入故事,最後你會願意交換某些條件,生活在這個美麗新世界嗎?」AK一頓再說,每個人也有權利選擇自己的善良,但每個人心中善良的尺也不一樣,不能以己度人:「你問我的話……我應該不會選擇那個新世界,我還是會堅持自己,做一些覺得正確的事。」謝家祺則表示,他的答案如向榮:「電影最後的第一天是留給我們,回到日常,而日常又是怎樣?」AK說:「無論經歷的事情是甚麼也好,90分鐘最後的抉擇是留給各位觀眾自己體驗。」
而你,又會否願意付出代價,交換一張生活於美麗新世界的門票?
Lorraine Lam @HairCulture
Yumi Cheung @Annie G. Chan Makeup Centre
服裝:Y-3, Giuseppe Zanotti
造型:PIPA Creative
場地提供: 太子酒店